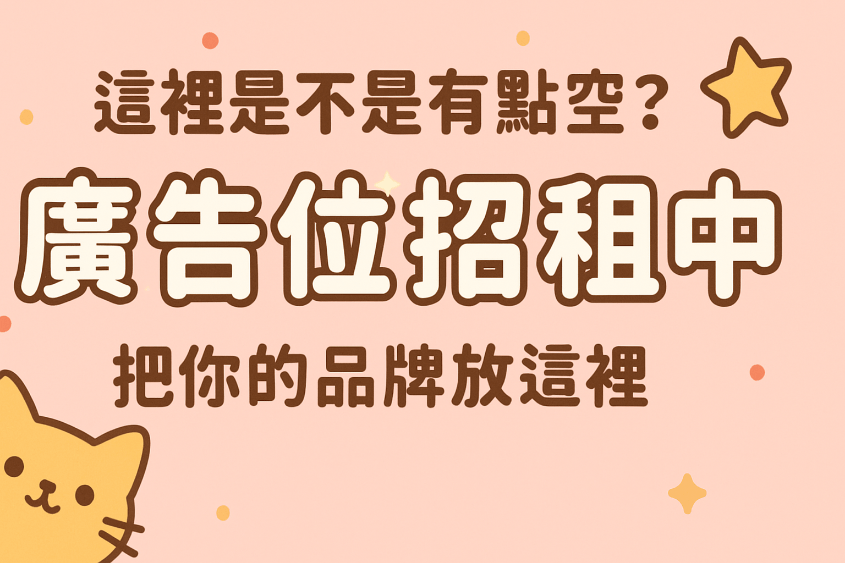【經】阿難白佛言:世尊!若此見精,必我妙性。今此妙性,現在我前?見必我真,我今身心,復是何物?
白話翻譯:「阿難稟告佛陀說:『世尊!如果這個能見的精華(見精),必定就是我那不可思議的真實本性(妙性)。那麼,現在這個真實的本性,難道是顯現在我面前的一個東西嗎?如果說「能見」才是我真實的自體,那麼我現在這個身體和能分別的念想之心,又算是什麼東西呢?』」
補充說明:經過前幾番的辯論,阿難開始領悟到「能見的自性」才是真實的,但他立刻陷入了新的困惑。他無法理解這個「真實的我」(見性)與「經驗中的我」(身心)之間的關係。如果見性是真我,那這個能被感知、能思考的身體和心念,又是什麼?他誤將「見性」當作一個可以與身心對立的、在「我面前」的客體,從而產生了身心與真性分裂的困惑。
名詞解釋:
- 見精:能見的精華。指見性的精微、純粹、靈妙的體性,不同於眼根的物質性。
- 妙性:不可思議的、微妙的真實本性,即佛性、真如自性。
- 現在我前:顯現在我的面前。阿難此時將「見性」物化、對象化了。
- 身心:指眾生的色身(物質身體)和受、想、行、識等心理活動的總和。
- 復是何物:又是什麼東西呢?
【經】而今身心,分別有實;彼見無別,分辨我身。若實我心,令我今見,見性實我,而身非我?何殊如來,先所難言:物能見我。惟垂大慈,開發未悟。
白話翻譯:「『而現在我這個身體和心念,都能夠被清晰地分別,似乎各有實體;但那個能見的自性本身卻是圓融無礙、沒有分別的,但它又能反過來分辨出我的身體。如果(這個能見的自性)真是我(能分別)的心,它又讓我現在能夠看見(這個見性),這就變成了「能見的自性」是我,而「這個身體」卻不是我了?這種情況,與如來您先前詰難我所說的「物能見我」(我看見物,物也看見我)的矛盾道理,又有什麼差別呢?懇請世尊垂憐您的大慈悲,開啟點化我尚未覺悟的地方。』」
補充說明:阿難的困惑加深。他觀察到:1. 身心可被分別,但見性本身無分別。2. 若見性是真我,而這個真我又能被「我」(現在這個能思考的我)所見,那就出現了「能見的我」和「被見的我」,造成了自我分裂。他覺得這與佛陀之前破斥過的「物我相對」的矛盾邏輯很相似,因此懇請佛陀為他解開這個迷惑。
名詞解釋:
- 分別有實:能夠被分別,好像有實體一樣。
- 彼見無別:那個能見的自性本身卻是沒有分別的。
- 分辨我身:(見性)卻能反過來分辨出我的身體。
- 何殊:有什麼差別?
- 惟垂大慈:懇請您垂憐、施予大慈悲。
- 開發未悟:開啟點化尚未覺悟之處。
【經】佛告阿難:今汝所言,見在汝前,是義非實。若實汝前,汝實見者,則此見精,既有方所,非無指示?
白話翻譯:「佛陀告訴阿難:『你現在所說的,「能見的自性」在你的面前,這個觀點是不真實的。如果它真的在你的面前,而且你確實看見了它,那麼這個能見的精華,既然有了一個確切的方位處所,那它就不是一個無法被指示出來的東西了,對嗎?』」
補充說明:佛陀直接否定了阿難「見在汝前」的看法,指出這是將「見性」物化的錯誤。佛陀開始引導阿難:任何一個有具體方位和處所(方所)的「東西」,都必定是可以被明確指示出來的。既然你認為「見」在你的面前,那它就應該可以被指出來。
名詞解釋:
- 是義非實:這個觀點、道理是不真實、不正確的。
- 方所:方位和處所,指具體的位置。
- 非無指示:不是不能被指示出來。雙重否定表示肯定,意即「必定可以被指示出來」。
【經】且今與汝,坐祇陀林,遍觀林渠,及與殿堂,上至日月,前對恒河。汝今于我師子座前,舉手指陳是種種相:陰者是林,明者是日,礙者是壁,通者是空,如是乃至草樹纖毫,大小雖殊,但可有形,無不指著。
白話翻譯:「『暫且不說別的,現在我與你同坐在祇陀林中,放眼望去,遍處是樹林、溝渠以及殿堂,抬頭可以看見日月,前面對著恒河。你現在就在我的師子座前,可以舉起手來一一指陳這各種各樣的物相:那蔭涼的是樹林,那光明的是太陽,那阻礙視線的是牆壁,那通達無礙的是虛空,像這樣乃至於一草一木、一絲一毫,它們的大小雖然各不相同,但只要是具有形狀相貌的,沒有一個是你不能指出來的。』」
補充說明:佛陀用當下環境中的一切事物為例,向阿難說明:凡是客觀存在的「物」(有相),無論是具體的(林、日、壁)還是抽象的(空),都可以被明確地指示出來。這是佛陀為接下來的詰問所做的鋪墊,即要求阿難也用同樣的方式指出「見」為何物。
名詞解釋:
- 林渠:樹林與溝渠。
- 恒河 (Gaṅgā):印度著名的聖河。
- 師子座:即獅子座,佛說法時所坐的座位,比喻佛說法無畏,能降伏一切外道,如獅子為百獸之王。
- 指陳:用手指著並陳述說明。
- 陰者、明者、礙者、通者:指呈現蔭涼、光明、阻礙、通達等不同屬性的事物。
- 纖毫:指極其微小的東西。
- 指著:指點出來。
【經】若必其見,現在汝前,汝應以手,確實指陳,何者是見?
白話翻譯:「『如果這個能見的自性,確定是顯現在你的面前,那麼你也應該能夠用手,確實地指出來,到底哪一個是「見」呢?』」
補充說明:佛陀發出了直接的挑戰:既然你認為「見」在你面前,而且凡是在面前的物相都可以被指出,那麼,請你現在就用手指出「見」到底是什麼。這個問題的設計,旨在讓阿難親身體悟到,「見性」並非一個可以被當作客觀對象來指陳的「東西」。
名詞解釋:
- 何者是見:哪一個東西是「能見的自性」?
【經】阿難當知:若空是見,既已成見,何者是空?若物是見,既已是見,何者為物?汝可微細,披剝萬象,析出精明,淨妙見元,指陳示我。同彼諸物,分明無惑。
白話翻譯:「『阿難你應當知道:如果說「虛空」就是「見」,那麼既然虛空已經成了能見的自性,那什麼又是被你所見的「虛空」呢?如果說「物體」就是「見」,那麼既然物體已經成了能見的自性,那什麼又是被你所見的「物體」呢?你可以試著仔細地、層層地剖析剝離這萬千物象,從中分析出那個精純、光明、清淨、微妙的見性本元,將它指出來給我看看,讓它就像那些物體一樣,能夠被分明地認識而沒有任何疑惑。』」
補充說明:佛陀進一步封堵了所有可能的回答。指出「見」與「所見之物」不能混為一談。如果說空是見,那麼能見的「見」和所見的「空」就混淆了;如果說物是見,能見的「見」和所見的「物」也混淆了。佛陀要求阿難從萬物中,將「見性」這個純粹的「能見者」,像分揀豆子一樣,從被見的萬物中剝離出來,單獨指出。這實際上是在引導阿難認識到,「見性」與「萬物」的關係是「非一非異」的,它遍在萬物之中,卻又不是萬物本身。
名詞解釋:
- 何者是空 / 何者為物:什麼又是(被你看見的)虛空/物體呢?指出能見與所見不能是同一個。
- 披剝萬象:層層地剖析剝離萬千物象。
- 析出:分析、分離出來。
- 精明,淨妙見元:指能見之性(見性)的本元,其特質是精純、光明、清淨、微妙。
- 同彼諸物,分明無惑:像那些(被你所見的)物體一樣,可以被清晰地分辨認識,而沒有任何疑惑。
【經】阿難言:我今於此,重閣講堂,遠洎恒河,上觀日月,舉手所指,縱目所觀指皆是物,無是見者。
白話翻譯:「阿難說:『我現在在這座重閣講堂之中,遠至恒河,上觀日月,凡是我能舉手指示的,以及放眼所能觀看的一切,指出來的通通都是「物」,沒有一個是那個「能見的自性」(見)。』」
補充說明:在佛陀的引導和挑戰下,阿難自己得出了結論。他審視了所有能感知到的對象,發現它們都屬於「所見的物」,而能發出「看」這個動作的「能見者」本身,卻無法在這些物象中被指陳出來。他體悟到「見」與「物」的區別。
名詞解釋:
- 洎 (jì):及,至。
- 縱目所觀:放眼所能觀看的。
- 指皆是物,無是見者:指出來的全都是「物」(被看的對象),沒有一個是「見」(能看的主體)。
【經】世尊!如佛所說,況我有漏,初學聲聞;乃至菩薩,亦不能于萬物象前,剖出精見,離一切物,別有自性。
白話翻譯:「『世尊!正如佛陀您所開示的那樣,何況我還只是一個尚有煩惱(有漏)、初發心修學的聲聞弟子;即便是道行高深的菩薩,恐怕也不能在萬千物象面前,將那精純的「見性」從中剖析出來,讓它離開一切物象,而單獨地另有一個自體存在。』」
補充說明:阿難的領悟更深一層。他不僅承認自己做不到,更推及到更高果位的菩薩,認為即便是菩薩,也無法將「見性」作為一個獨立的實體從萬物中剝離出來。這表明他開始意識到,「見性」與「萬物」之間是一種遍在而又不可分割的關係,並非一個可以被單獨拿出來的「東西」。
名詞解釋:
- 有漏 (Sāsrava):指尚有煩惱、未斷盡生死流轉因緣的狀態。相對的是「無漏」。
- 聲聞 (Śrāvaka):聽聞佛陀言教之聲而悟道者,是小乘佛教的修行人。
- 菩薩 (Bodhisattva):指發心上求佛道、下化眾生的覺有情。
- 剖出精見:將精純的見性剖析、分離出來。
- 離一切物,別有自性:離開一切物象,而另外單獨有自己的體性。
【經】佛言:如是如是!佛復告阿難:如汝所言,無有見精,離一切物,別有自性,則汝所指,是物之中,無是見者。
白話翻譯:「佛陀說:『是這樣的,是這樣的!』佛陀又告訴阿難:『正如你所說,並沒有一個能見的精華,可以離開一切物象而單獨另有自體存在,那麼,在你所指的這些物體之中,確實也就沒有一個是那個能見的自性。』」
補充說明:佛陀首先兩次肯定(「如是如是!」)了阿難的領悟,即「見」不可離物而獨存,同時「見」也不等於物。這句話總結了第一階段的辯論:在「物」裡面找不到「見」,也無法從「物」當中把「見」分離出來。
名詞解釋:
- 如是如是:佛經中,佛陀用來表示極度肯定和讚許的說法。
【經】今復告汝:汝與如來,坐祇陀林,更觀林苑,乃至日月,種種像殊,必無見精,受汝所指,汝又發明,此諸物中,何者非見?
白話翻譯:「『現在我再告訴你:你與如來一同坐在祇陀林中,再次觀察這些林園,乃至日月等種種形相各異的物體,既然確定沒有一個能見的精華,可以被你指出來,那麼,你再發明(闡明)一下,在所有這些物體當中,又有哪一個「不是」能見的自性呢?』」
補充說明:佛陀的提問進入了更深、更具顛覆性的一層。在確認了「物非是見」之後,佛陀反過來問「何者非見」(哪個不是見?)。這個問題旨在引導阿難從另一個角度思考:既然見性遍在一切處,那麼在你所見的萬物中,又有哪一樣東西是能脫離你的「見」而獨立存在的呢?換言之,萬物是否皆是「見」之所現?
名詞解釋:
- 更觀:再次觀察。
- 像殊:形相各不相同。
- 受汝所指:被你所指出來。
- 汝又發明:你再闡明、開示一下。
- 何者非見:哪一個東西「不是」見?
【經】阿難言:我實遍見,此祇陀林,不知是中,何者非見。何以故?若樹非見,云何見樹?若樹即見,復云何樹?
白話翻譯:「阿難說:『我確實是遍見了這整個祇陀林,但我不知道這其中,到底哪一樣東西「不是」見。這是什麼緣故呢?因為如果說樹木「不是」見,那我又如何能看見樹木呢?(看不見的東西,無法說它存在);但如果說樹木「就是」見,那又把真正的樹木稱作什麼呢?(能見與所見又混淆了)』」
補充說明:阿難面對佛陀的新問題,再次陷入了兩難。他發現,他所見的一切,都離不開他的「見」,所以他無法指出哪樣東西「不是」見。但他同時又明白,如果直接說物體「就是」見,又會陷入能所不分的矛盾。這段獨白非常精彩地展現了阿難在逼近真理時的思辨過程。
名詞解釋:
- 遍見:普遍地看見,看遍。
- 不知是中,何者非見:不知道這其中,哪個東西不是見。
- 云何見樹:怎麼能看見樹呢?(如果樹與見無關)
- 復云何樹:又把什麼稱作樹呢?(如果樹就是見)
【經】如是乃至,若空非見,云何見空?若空即見。復云何空?我又思惟:是萬象中,微細發明,無非見者。
白話翻譯:「『像這樣乃至於,如果說虛空「不是」見,那我又如何能看見虛空呢?但如果說虛空「就是」見,那又把什麼稱作虛空呢?我又仔細地思考:在這萬千物象之中,經過仔細地發掘闡明,似乎沒有一樣東西「不是」那能見的自性所顯現的。』」
補充說明:阿難將「樹」的例子推及到「空」,得出同樣的兩難結論。最終,他得出了第二個階段性的、更為深刻的領悟:在仔細思辨之後,他發現萬物似乎都離不開「見」,甚至可以說萬物「無非是見」(沒有一樣不是見)。這與他第一階段「無是見者」(沒有一樣是見)的領悟,形成了一對看似矛盾卻相輔相成的觀點。
名詞解釋:
- 微細發明:仔細地、深入地去發掘闡明。
- 無非見者:沒有一樣不是「見」的(所現)。
【經】佛言:如是如是!於是大眾,非無學者,聞佛此言,茫然不知,是義終始!一時惶悚,失其所守。
白話翻譯:「佛陀說:『是這樣的,是這樣的!』聽到佛陀這樣肯定阿難的結論,在座的大眾中,那些尚未證得無學果位的修行人(非無學者),聽了佛陀這番對話,都感到茫然不解,完全不知道這些義理的頭緒和歸結之處!他們一時之間感到既惶恐又悚懼,失去了平常所持守的修行準則和見解。」
補充說明:佛陀再次以「如是如是」印證了阿難的領悟。然而,這種「是見」與「非見」的辯證法,對於根基較淺的聽眾來說過於高深,使他們陷入了巨大的困惑和恐慌之中。他們平日所依賴的「心」、「物」等基本概念被徹底顛覆,導致他們暫時失去了修行的方向(失其所守)。
名詞解釋:
- 非無學者:指尚未達到「無學」果位的修行人。在小乘中,「無學」指阿羅漢,已無需再修學;「有學」則指初果至三果的聖者。此處泛指在座的所有未究竟解脫者。
- 是義終始:這些義理的開端與終結,指其來龍去脈、頭緒與歸結。
- 惶悚 (huáng sǒng):惶恐、恐懼。
- 失其所守:失去了平日所持守的信念、見解或修行方法。
【經】如來知其魂慮變懾,心生憐愍,安慰阿難,及諸大眾:諸善男子!無上法王,是真實語,如所如說,不誑不妄,非末伽黎,四種不死,矯亂論議;汝諦思惟,無忝哀慕!
白話翻譯:「如來知道他們心神不定、驚懼不安,心中生起了憐憫,於是安慰阿難以及在座的大眾說:『各位善男子!至高無上的法王(佛陀),所說的都是真實不虛的語言,是如其本然而說,既不欺騙也不虛妄,絕非像末伽黎(外道之一)那樣,提出四種關於「不死」的、狡猾混亂的戲論。你們應當仔細地思惟,不要辜負了你們那份哀求仰慕佛法的心!』」
補充說明:佛陀洞察到大眾的驚恐,立刻給予安慰。他強調自己所說的是真實語,是究竟的實相,並非當時印度流行的某些外道的詭辯(矯亂論議)。他鼓勵大眾不要害怕,應當靜心深思,因為這才是他們所追求的真實解脫之道。
名詞解釋:
- 魂慮變懾:心神思慮變得驚恐不安。
- 無上法王:對佛陀的尊稱,因佛於一切法得大自在,如王中之王。
- 不誑不妄:不說欺騙之語,不說虛妄之言。
- 末伽黎 (Makkhali Gosāla):古印度「六師外道」之一,持「無因無緣」的宿命論,其論點被佛教判為「矯亂論」,認為其言論狡猾,混亂視聽,不能導向解脫。此處的「四種不死矯亂論議」是其詭辯論之一。
- 汝諦思惟:你們應當仔細地思惟。
- 無忝哀慕 (wú tiǎn āi mù):「忝」是辜負、玷污。「哀慕」指哀求和仰慕(佛法)的心。意為不要辜負了你們這份求法之心。
【經】是時,文殊師利法王子,愍諸四眾,在大眾中,即從座起,頂禮佛足,合掌恭敬,而白佛言:世尊!此諸大眾,不悟如來,發明二種,精見、色、空,是、非是義。
白話翻譯:「這個時候,被尊為法王之子的文殊師利菩薩,哀憫在座的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等四眾弟子,在大眾之中,立即從座位上站起來,向佛陀行頂禮佛足之禮,然後雙手合掌,恭敬地對佛陀說:『世尊!在座的這些大眾,沒有能領悟如來您所開示闡明的,關於「能見的精華」(精見)與「所見的色相、虛空」(色、空)之間,「是」與「不是」這兩種相互關聯的義理。』」
補充說明:在法會陷入僵局之時,代表大智慧的文殊師利菩薩應時而起,他的角色是「代眾啟請」。他準確地指出了大眾困惑的核心:無法理解「見」與「境」(色、空)之間「是」與「不是」的辯證關係,即「物非是見」與「物無非見」這看似矛盾的兩個結論。
名詞解釋:
- 文殊師利法王子 (Mañjuśrī-kumārabhūta):文殊師利菩薩,以大智慧著稱。因其將繼承佛陀法身慧命,故尊稱為法王子。
- 愍 (mǐn):哀憫,憐憫。
- 四眾:指佛教的四類基本信眾:比丘(男出家眾)、比丘尼(女出家眾)、優婆塞(男在家眾)、優婆夷(女在家眾)。 - 精見、色、空:指能見的「見性」、所見的「有形色相」和所見的「虛空」。
- 是、非是義:指「是它」與「不是它」的辯證義理。
【經】世尊!若此前緣色空等像,若是見者,應有所指,若非見者,應無所矚。而今不知是義所歸,故有驚怖!非是疇昔,善根輕鮮。
白話翻譯:「『世尊!如果眼前所攀緣的這些色相、虛空等物象,它「是」能見的自性,那麼就應該能夠被指出來;如果它「不是」能見的自性,那麼就應該什麼也看不見(應無所矚)。大眾現在不知道這個義理的歸結之處到底在哪裡,所以才會產生驚慌和恐懼!這並非是因為他們過去所種的善根太過輕微淺薄的緣故。』」
補充說明:文殊菩薩為大眾辯護,並清晰地闡述了他們的邏輯困境:按照常理,一個東西要嘛「是」,要嘛「不是」。如果物象是見,就該能被指出來(但阿難已證明不能);如果物象不是見,那它就應與見無關,理應看不見它(但明明看見了)。正是這種非此即彼的邏輯無法解釋眼前的矛盾,才使大眾驚怖。文殊菩薩強調,這不是他們善根不夠,而是法義太過深奧。
名詞解釋:
- 前緣:眼前的、所攀緣的對象。
- 應無所矚:應該什麼也看不見。矚,注視,看見。
- 是義所歸:這個義理的歸結、落腳點。
- 疇昔 (chóu xī):往昔,從前。
- 善根輕鮮:善根(修行的基礎)輕微、鮮少。
【經】惟願如來,大慈發明,此諸物象,與此見精,元是何物?於其中間,無是?非是?
白話翻譯:「『惟願如來您,能以大慈悲心,為我們開示闡明:這一切物象,與這個能見的精華,它們本元究竟是什麼東西?在這兩者之間,為什麼既沒有「是」的關係,也沒有「不是」的關係呢?』」
補充說明:文殊菩薩最後提出了兩個核心問題,代大眾向佛祈請:1. 見精和物象,它們的本質(元是何物)到底是什麼?2. 為何它們之間是一種超越了「是」與「不是」的邏輯關係?這個提問直指核心,為佛陀接下來的究竟開示創造了契機。
名詞解釋:
- 元是何物:本來、究竟是什麼東西?
- 於其中間,無是?非是?:在這兩者之間,為什麼沒有「是」的關係?也沒有「不是」的關係呢?
【經】佛告文殊及諸大眾:十方如來,及大菩薩,于其自住三摩地中,見與見緣,並所想相,如虛空華,本無所有。
白話翻譯:「佛陀告訴文殊師利以及在座的大眾:『十方世界的一切如來,以及諸大菩薩,在他們安住於甚深禪定(三摩地)的境界當中時,(所觀照到的)能見的自性(見)、所見的對象(見緣),以及由此所生的一切心念想象(所想相),都如同眼睛有毛病時所看見的虛空中的花朵(虛空華)一樣,從本體上來看是虛幻不實、本來無所有的。』」
補充說明:佛陀在此給出了究竟的答案。他指出,從已證悟的佛菩薩境界來看,眾生所執著的一切——包括能看的「見」、所看的「物」(見緣)和能想的「心」(所想相)——都非實有,其性質如同「空華」一般,是因緣和合的幻相,沒有永恆不變的實體。
名詞解釋:
- 自住三摩地:安住於自己甚深的禪定境界之中。
- 見與見緣:「見」指能見的見性、主觀的覺知;「見緣」指見性所攀緣的對象,即所見的客觀世界。
- 所想相:心中所生起的一切思維、想象和概念。
- 虛空華 (ākāśa-puṣpa):又作空華。比喻本來沒有而因某種錯覺(如眼病)顯現的虛幻之物。
- 本無所有:從根本上來說是沒有實體的。
【經】此見及緣,元是菩提,妙淨明體,云何於中,有是、非是?
白話翻譯:「『這個能見的自性以及它所攀緣的對象,它們的本元,其實都是那無上覺悟(菩提)的、不可思議的、清淨光明的本體。既然它們本體相同,又怎麼能在那其中,強行分別出哪個「是」它,哪個「不是」它呢?』」
補充說明:佛陀進一步揭示了「空華」的本質。雖然見與見緣是幻相,但它們並非與真心無關。它們的本元、它們賴以顯現的基底,就是「菩提妙淨明體」(即常住真心、真如佛性)。就如同波浪(幻相)的本體是水(實相)一樣。既然見與緣的本體都是同一個真心,那麼在這之上做「是」與「不是」的二元對立劃分,就失去了意義。
名詞解釋:
- 菩提,妙淨明體 (Bodhi-citta-prakṛti-pariśuddha-prabhāsvara):指眾生本具的覺性、佛性。菩提(覺悟)、妙(不可思議)、淨(清淨無染)、明(光明能照)、體(本體)。
- 云何於中,有是、非是:怎麼能在那其中,有「是它」或「不是它」的分別呢?
【經】文殊,吾今問汝:如汝文殊,更有文殊,是文殊者?為無文殊?
白話翻譯:「『文殊,我現在問你:就好像你就是文殊,那是否還有另外一個文殊?這個(另外的文殊)是文殊呢?還是沒有文殊呢?』」
補充說明:佛陀用文殊自身來做比喻,以幫助他和大眾理解。佛陀的問題設計得非常巧妙,意在引導文殊思考「真我」與「假名」的關係,以及「一」與「異」的問題。
名詞解釋:
- 如汝文殊:就好像你就是文殊。
- 更有文殊:還有另外一個文殊嗎?
- 是文殊者?為無文殊?:(如果有的話)那個是文殊嗎?還是說(根本就)沒有另外一個文殊?
【經】如是,世尊!我真文殊,無是文殊。何以故?若有是者,則二文殊,然我今日,非無文殊,於中實無,是非二相。
白話翻譯:「(文殊菩薩回答說:)『是的,世尊!我就是真正的文殊,並沒有另外一個所謂「是文殊」的文殊。這是什麼緣故呢?因為如果真的有另外一個「是文殊」,那麼就變成有兩個文殊了。然而,我今天,並非不存在(我就是文殊),但在我這個真實的文殊自體之上,實在是沒有「是文殊」和「非文殊」這兩種對立的相狀。』」
補充說明:文殊菩薩以其大智慧,完美地回答了佛陀的問題。他指出:1. 我就是文殊,這是事實。2. 但不能在我這個真實的文殊之外,再安立一個概念上的「是文殊」,否則就成了二元對立,會有兩個文殊。3. 在「我就是文殊」這個事實中,既沒有「是」的標籤,也沒有「非是」的對立。真實的自體是超越這種概念分別的。
名詞解釋:
- 我真文殊,無是文殊:我就是真正的文殊,但沒有另外一個需要被標籤為「是文殊」的文殊。
- 則二文殊:那就變成有兩個文殊了。
- 非無文殊:並非不存在文殊(我就是文殊)。
- 是非二相:「是」與「非」這兩種對立的相狀。
【經】佛言:此見妙明,與諸空塵,亦復如是。本是妙明,無上菩提,淨圓真心。妄為色空,及與聞見。
白話翻譯:「佛陀說:『這個不可思議、光明無礙的能見自性,與所有虛幻的塵境(如色、空等),其道理也是一樣的。它們的根本,都是那個不可思議、光明無礙的、至高無上的覺悟(菩提),那個清淨圓滿的真實之心。只是因為一念妄動,才變現出「色、空」等客觀塵境,以及「能聞、能見」等主觀知覺。』」
補充說明:佛陀將文殊的回答類比到「見」與「境」的關係上。指出「見」與「境」的根本都是同一個「淨圓真心」。真心本來清淨,只因「妄動」,才從這個一體真心中,虛妄地分別出能見的「見」和所見的「色、空」等對立的幻相。
名詞解釋:
- 空塵:指空幻不實的塵境,包括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六塵。
- 亦復如是:也是像這樣。
- 淨圓真心:清淨、圓滿的真實之心。
- 妄為:因為一念妄動而變現為...
- 色空,及與聞見:指客觀的物象(色)、空間(空),以及主觀的能聞、能見等感覺能力。
【經】如第二月,誰為是月?又誰非月?文殊,但一月真,中間自無是月非月。
白話翻譯:「『這就好比(因眼病或按壓眼球而看見的)第二個月亮,你能說哪個是「真月亮」,哪個又是「假月亮」嗎?文殊啊,其實只有一個月亮是真實的,在這真、假兩個月亮的幻象當中,本來就沒有「是真月」或「非真月」的實質可言(因為那第二個月亮根本就不存在)。』」
補充說明:佛陀用了著名的「第二月」的比喻來總結。天上的真月亮比喻「淨圓真心」,因眼病(無明妄動)而看見的第二個月亮,則比喻由真心所變現出的能見、所見等一切幻相。對於這個幻相(第二月),去討論它「是月」還是「非月」是沒有意義的,因為它的本質就是「無」。唯一的真實只有那個「一月真」。
名詞解釋:
- 第二月:因眼病(如翳)或用手指按壓眼球時,所看到的月亮的重影或幻象。比喻虛妄不實之相。
【經】是以汝今,觀見與塵,種種發明,名為妄想,不能於中,出是、非是。由是真精,妙覺明性,故能令汝,出指非指。
白話翻譯:「『因此,你現在去觀察能見的「見」與所見的「塵」,以及對它們之間關係的種種思辨闡明,這些(思辨本身)都名為「妄想」,你不可能在這些妄想的層面中,得出一個絕對的「是」或「不是」的結論。正因為有那個真實、精純、不可思議、覺悟光明的本性存在,所以才能讓你(阿難)在前面的問答中,既能「指出」(萬物皆是物,無是見者),又能「不指出」(萬物皆是見,無非見者)。』」
補充說明:佛陀做最後的總結:1. 所有關於「見」與「塵」的二元對立的思辨,其本身都屬於妄想的範疇,無法觸及實相。2. 阿難之所以能夠在前面的辯論中,從正反兩面(出指非指)來描述「見」與「物」的關係,正是因為這一切思辨和現象的背後,有那個超越了二元對立的「真精妙覺明性」作為根源。這個真性,既不是物,又遍在於物,所以才能產生「是」與「不是」都無法完全描述的甚深義理。
名詞解釋:
- 見與塵:能見的主體與所見的客觀塵境。
- 種種發明:種種的思辨和闡明。
- 出是、非是:得出「是它」或「不是它」的結論。
- 真精,妙覺明性:指真實精純、不可思議、覺悟光明的真如本性。
- 出指非指:既能指出(萬物都不是見),又能闡明無法指出(萬物都離不開見)。指阿難前面一正一反的兩種回答。
【經】阿難白佛言:世尊!誠如法王所說,覺緣遍十方界,湛然常住,性非生滅。與先梵志,娑毗迦羅,所談冥諦,及投灰等,諸外道種,說有真我,遍滿十方,有何差別?
白話翻譯:「阿難稟告佛陀說:『世尊!誠如法王(您)所說,這個能覺悟的真心,它所攀緣的對象遍滿十方世界,它自身湛然清淨、永恆常住,其體性是不生不滅的。那麼,這個說法與從前印度的婆羅門修行人(梵志),如數論派的創始人迦毗羅(娑毗迦羅)所談論的「冥諦」(宇宙最初的、幽暗不明的本體),以及那些塗灰外道(投灰等)等各種外道流派,他們所說的有一個「真我」遍滿十方世界,這兩種觀點之間,究竟有什麼差別呢?』」
補充說明:在佛陀開示了真心的體性之後,博聞強記的阿難立刻聯想到了當時印度的其他哲學和宗教流派(外道)。他發現佛陀所說的「真心遍滿常住」,在字面上與某些外道(如數論派、我論者)所說的宇宙本體(冥諦)或永恆真我(真我)非常相似。他感到了困惑,擔心會將佛法與外道見解混淆,因此提出了這個非常重要的問題,請求佛陀辨明其間的根本差別。
名詞解釋:
- 覺緣:此處指能覺悟的真心及其所緣的境界,合指覺性。
- 湛然常住 (zhàn rán):湛然,指清淨、不動、湛深。形容真心清淨不動、永恆存在。
- 性非生滅:其體性是不生也不滅的。
- 梵志 (Brāhmaṇa):指古印度婆羅門教的修行人,以清淨梵行為志。
- 娑毗迦羅 (Kapila):即迦毗羅,古印度數論派(Sāṃkhya)的創始人。
- 冥諦 (Prakṛti):數論派的哲學概念,指宇宙萬物最初的、未顯現的、幽暗不明的根本原因或本體。
- 投灰等,諸外道種:指當時印度一些以塗灰等苦行作為修行方式的外道派別,他們也主張有一個永恆的「真我」。
- 真我 (Ātman):許多印度教派主張的宇宙終極實在或個人靈魂的本體,認為它是永恆、遍在、不變的。
【經】世尊亦曾於楞伽山,為大慧等,敷演斯義:彼外道等,常說自然,我說因緣,非彼境界。
白話翻譯:「『而且世尊您也曾經在楞伽山上,為大慧菩薩等人,詳細地演說過這個義理:那些外道們,常常主張「自然」(萬物是無因而然、自己如此的),而我(佛法)所說的是「因緣」(萬法皆由因緣條件和合而生),這與他們的境界是完全不同的。』」
補充說明:阿難引用了佛陀在另一部重要經典《楞伽經》中的教誨來加強他的疑問。他記得佛陀曾明確區分佛法與外道的根本不同在於:佛法講「緣起(因緣)」,而外道講「自然」或「神我」等。這讓他更加困惑,因為現在所聽到的「真心不生不滅、湛然常住」,聽起來非常像是「自然」,而非「因緣」。
名詞解釋:
- 楞伽山 (Laṅkā):斯里蘭卡的一座山,傳說是佛陀宣講《楞伽經》的地方。
- 大慧 (Mahāmati):大慧菩薩,《楞伽經》中的主要提問者。
- 敷演斯義:詳細地演說這個義理。
- 自然 (Svabhāva):指事物無因而生,或自有其性,自己如此,不依賴其他條件。這是佛法所破斥的一種外道見解。
- 因緣 (Hetu-pratyaya):指構成事物存在和變化的主要條件(因)和次要條件(緣)。萬法因緣生,是佛教的核心教義之一。
【經】我今觀此:覺性自然,非生非滅,遠離一切虛妄顛倒,似非因緣,與彼自然;云何開示,不入群邪,獲真實心,妙覺明性?
白話翻譯:「『我現在觀察這個(您所說的)覺性,它(聽起來)像是「自然」的,因為它不生不滅,遠離了一切虛妄顛倒。這似乎不是「因緣」所生,但(為了區別)又好像應該與外道的「自然」不同。究竟要如何開示,才能讓我們不致於落入那些邪見之中,而能真正獲得那個真實之心、那個不可思議的、覺悟光明的本性呢?』」
補充說明:阿難道出了他的核心困境:這個「覺性」,從其「不生不滅」的特性來看,似乎不屬於「因緣」範疇(因緣所生法是生滅的),而非常接近外道的「自然」論。但他又知道佛法非外道。所以他懇請佛陀開示一條明路,闡明覺性「非因緣、非自然」的甚深義理,使大家能正確理解,不落邪見,從而證得真心。
名詞解釋:
- 覺性自然:(這個)覺性(聽起來像是)「自然」的。
- 似非因緣,與彼自然:(覺性)好像不是因緣所生,(但為了區別)又應該與他們的「自然」論不同。
- 不入群邪:不落入各種外道的邪見之中。
- 獲真實心,妙覺明性:證得、獲得那個真實之心、不可思議的覺悟光明之性。
【經】佛告阿難:我今如是,開示方便,真實告汝,汝猶未悟,惑為自然!
白話翻譯:「佛陀告訴阿難:『我現在已經像這樣,用了種種善巧方便來為你開示,把真實的道理告訴了你,而你卻仍然沒有覺悟,還被「自然」這種觀念所迷惑!』」
補充說明:佛陀略帶責備地指出阿難的問題所在:雖然佛陀已經用了各種方式(如前面的七處徵心、辨見是物非物等)來層層開示,但阿難仍然停留在用「因緣」或「自然」等世間的二元對立概念來揣度那超越言詮的「真心」,所以始終無法真正契入。
名詞解釋:
- 開示方便:用善巧方便的方法來開示。
- 猶未悟:仍然沒有覺悟。
- 惑為自然:被「自然」這種見解所迷惑。
【經】阿難!若必自然,自須甄明,有自然體。汝且觀此,妙明見中,以何為自,此見為復以明為自?以暗為自?以空為自?以塞為自?
白話翻譯:「『阿難!如果這個見性必定是「自然」的,那麼它自己必須要能被審察辨明,有一個固定不變的「自然之體」。你姑且觀察一下,在這個不可思議、光明的能見自性當中,它究竟是以什麼作為它自己的體性呢?這個見性,是把「光明」當作它的自體呢?還是把「黑暗」當作它的自體?是把「虛空(通)」當作它的自體?還是把「堵塞(礙)」當作它的自體呢?』」
補充說明:佛陀開始正式破斥「自然」見。他指出,任何一個所謂「自然」的東西,都必須有一個獨立不變的自體(自然體)。佛陀隨即提出一連串問題,要求阿難在「見性」中找出這個固定的自體。他列舉了幾對相互對立的屬性(明/暗、空/塞),讓阿難思考見性是否以其中任何一個為其不變的自體。
名詞解釋:
- 甄明 (zhēn míng):審察、辨明。
- 自然體:「自然」的體性或實體。
- 以何為自:以什麼作為它自己的體性。
- 以明為自 / 以暗為自 / 以空為自 / 以塞為自:以光明/黑暗/虛空/堵塞作為它的自體。
【經】阿難!若明為自,應不見暗;若復以空為自體者,應不見塞;如是乃至,諸暗等相,以為自者,則于明時,見性斷滅,云何見明?
白話翻譯:「『阿難!如果見性是以「光明」為它的自體,那麼當面對黑暗時,它就應該看不見黑暗(因為它的體性與暗相違);如果它又是以「虛空(通)」為它的自體,那麼當面對堵塞時,它就應該看不見堵塞。像這樣依此類推,如果見性是以「黑暗」等(與光明相對的)物相作為它的自體,那麼在光明出現的時候,這個見性豈不就因為它的自體(黑暗)消失而斷滅了嗎?如果見性斷滅了,又如何能看見光明呢?』」
補充說明:佛陀在這裡做了精闢的論證,證明「見性」不可能是「自然」的。因為:1. 如果見性的自體是A,那麼它就不能覺知與A相反的非A。但事實上,見性能夠了知光明,也能了知黑暗;能夠了知通達,也能了知堵塞。2. 如果見性的自體是A,那麼當A這個境界消失時(如黑暗消失,光明出現),見性本身也應該隨之斷滅。但事實上,見性在明暗等境界的轉變中,始終存在,並未斷滅。結論:既然見性沒有一個固定不變的「自體」,那它就不是外道所說的「自然」。
名詞解釋:
- 應不見暗:應該就看不見黑暗。
- 見性斷滅:能見的自性就斷絕消滅了。
- 云何見明:怎麼還能看見光明呢?